周重林:《茶经》与茶人的修养

(本文节选自周重林《茶之基本:陆羽茶经启示录》,原标题:茶人的修养——来自陆羽《茶经》的启示)
陶渊明不懂音律,但他觉得琴雅,家中有一张无弦琴,每次喝完酒,便在无弦琴上来回拔,乐琴书以消忧。对来访的客人,不论是谁,只要有酒,他一定摆酒待客。他如果先喝醉了,就告诉客人说:“我醉了,要去睡个觉,你可以走了。”
自孔夫子倡导琴有助于乐教以来,后世许多不弹琴的士大夫家里,也会摆放琴以体现自己对教养的重视。
苏东坡不解棋,却喜欢听落子声。在古松流水间,听棋敲盘,自怡自得。吕行甫不会书写,但喜欢藏墨。东坡说,蔡襄老病不能饮茶,但经常烹茶玩玩。
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观看明末清初王铎的书法,胸中会涌起一股和谐愉悦之情。明人作画,多为稻粱谋,祝枝山、唐伯虎、徐文长都把书画换作了酒钱,这可悲么?
也许并非如此。王铎说用自己卖字换的钱,买了米养家,所购之墨却很糟糕,加上写字的时候,孩子在一边玩耍,大哭大闹,就有些烦,但书写还是要继续下去,是不是?
我们总是以为,琴棋书画沾不上半点烟火气息,但王铎的现实却是大部分人的现实。并非在深山、在松涛云影中挥洒出来的才是艺术。想想,现在中年的写作者,哪一个不是在王铎的状态下创作呢?
现实中,还有更过分的:“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
远在一千多年前,《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815—907)就面对过这样的处境,家人抱怨他为了收藏书画,弄得破衣粗食,做这些无益的事,到底图个啥?
张彦远回答说:“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能悦有涯之生?”当代美术史家范景中评价张彦远的这十六个字,并揣摩出非常重要的发现:“似乎是整个文明史上第一次对艺术表达了一种超物质目的的观念,暗示出一种伦理的哲学:艺术是一切人类成就的典范,因此可以修正道德价值的尺度;简言之,艺术由于可以净化身心,因此能够成为对抗野蛮、对抗低俗的解毒剂。”
张彦远从爱好到痴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
读书人,正是在俗事缠身之中,才把琴棋书画发展成从器而道的精神史。琴棋书画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更是脱俗的。
青木正儿在考证中国“琴棋书画”起源的时候说:“粗略回顾一下这一自成体系的熟语的变迁,四者都作为文雅艺术,被约定俗成地暗指为知识阶层的精神史。最早被开始熟用的是‘琴书’一词,‘书’所指的‘书籍’大约是其原义。读书累了则鼓琴解闷,这一生活常态大概是产生这一熟语的原因。读书本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长,作为第二特长,学琴就成了最受重视的风习。这从‘琴书’并称自可窥见。后来,‘琴书’的‘书’意谓书艺,反映了书法成为紧继琴艺后与知识分子密不可分的生活内容而广受重视。于是同气相求,琴艺邀请了棋艺,棋艺招徕了画艺,至此琴棋书画并称,一起代表着知识分子的雅游。”
在唐代,比张彦远早一些年出生的陆羽(733—约804),同样在为知识分子的痴癖做努力。然而茶与画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陆羽所面对的困难是,茶在当时还只是某种提神的小众饮品,因为僧人的推广才流行起来。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说,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位称降魔师的和尚大力提倡禅宗,和尚们坐禅时不能打瞌睡,不吃晚饭,但可以喝茶。和尚们各自携带着茶,到什么地方都煮茶喝。从此,人们互相仿效,喝茶就成了风俗。从邹、齐、沧、棣等州,直到京城,城镇里大都开设店铺煮茶卖,不管是僧道,还是世俗之人,都付钱取茶喝。茶叶从江淮一带运来,运茶的车船接连不断,存放处的茶叶堆积得像小山,品种数量很多。
在陆羽所处的时代,诗人对茶的书写远远不及画的万分之一。陆羽如果要把泡茶、品茶升格为高雅的艺术,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茶作为一种来源很正统的饮品,能被雅文化的主要群体普遍接受。
二、赋予茶教化的意义,能够让人“附庸风雅”。
陆羽首先做的事情是为“茶”正名,从“葭”“槚”“茗”“荼”“荈”这样的称谓中寻找“茶”的家族渊源,使世人相信茶有其历史,而不是训诂学家设下的思维陷阱。紧接着,陆羽追忆了在品茶链上的人,远追神农、伊尹,近溯杜育、王肃,饮茶史也就徐徐展开。
槚,《尔雅》解释说是“苦荼”,郭璞在为《尔雅》中的“槚”作注时,加了一句:“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小字一行,让茶的身份因时令而明确起来,“茗”是荼的芽,而“荈”是荼的老叶。陆羽对这些字做了详细的区别,“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
历代都有人根据只言片语来寻找茶曾经留给生活的痕迹,但都远远不及杜育《荈赋》所带来的这种格局,不如其令人满心喜悦。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
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
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
水则岷方之注,揖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酌之以匏,
取式公刘。
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烨若春敷。
若乃淳染真辰,色清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慷除。(□为佚文,选自沈冬梅《茶经校注》)
《荈赋》完整的叙述,奠定了陆羽茶学的基础,《荈赋》记载了茶的生长环境、种植的地理条件、采摘时令、泡茶的人群、茶具、茶汤的颜色以及品茶的感受,最后以茶的功效结尾。
晚摘为荈,吃的是叶子,而不是茶芽,这是时令。《荈赋》为饮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强调天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灵山、卷阿、丰壤、甘霖)、泡茶工具的选择(陶简、公刘匏),细致描写了茶汤的特点(华浮、积雪、春敷、清霜),择水(岷方之注、清流),功用(调神和内)。
唐之前的饮茶史,陆羽耗费了很多时间去考证,但那些只言片语只能缝补出一个小章节。杜育是开拓者,而陆羽是集大成者。《茶经》甫一面市,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陆羽还在世的时候,就被尊为“茶神”,被卖茶人供奉,与他的偶像、厨神伊尹一道调剂着华夏饮食的神经。
陆羽对茶的第二大改造在于工具。因为艺术依赖于工具,工具又会在不同的人手中发挥出截然不同的效果,这些工具就是后世总结的“陆氏二十四器”,也是陆羽真正的创造。
茶之法皆在二十四器中,这是封演在唐代的认知,也是我们今天的认知。这些器具来自厨房、酒桌、祭台、书房,但经过陆羽的改造后,都只有一个名字:茶器。这太容易理解了,书画需要笔墨纸砚,对弈需要棋子与棋盘,弹琴需要琴与琴台。传闻琴亦是神农所作,长三尺六寸,象征三百六十日;上圆下方,法天地。《白虎通》说:“琴以禁制淫邪,正人心也。”陆羽规制茶的器具,以饮茶来倡导君子之风,“精行俭德”,“目击而道存”。
二十四器的规模就足以令普通家庭望而生畏,注定了这只能是大户人家的配备。这些全新的茶器,因茶而生,是为把茶从世俗的吃法中解放出来。具体说来,《茶经》里记录的各种饮茶法,都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种:混饮与清饮。混饮,就是把茶与其他吃的混在一起煮,是谓“茗粥”,吃茶是为了补充热量。清饮就是只饮茶,茶是唯一的主角,饮茶为了提神。
在饮茶之前,陆羽会把绘有茶源、茶具、制法、茶器、泡法、茶事与产地的挂画准备好,让来的人知晓茶的来源、茶器的用途,引导大家去欣赏茶饼,教大家体会茶味层次。听起来很耳熟,对吗?这个场景就像今天的人去参加的某场茶会,陈列展架、产品以及产品手册都会告诉你茶产自何处,主持人会引导观众充分感受茶滋味……这些方式方法,其实都是陆羽的遗产。如今产茶地多了很多,制茶法变了很多,但核心的仪式从未发生过变化,这当然是陆羽了不起的地方,他贡献了一整套认知茶的方法论。
《茶经》是什么?就是茶的秩序。陆羽说某地的茶好,我们便说某茶地的茶好。陆羽说喝茶最好三四人一桌,我们便三四人一桌。
他说要先赏茶,于是我们赏茶。他说要赏器,于是我们赏器。他说要鉴水,于是我们鉴水。他说茶有回甘才好,于是回甘成为我们品茶的重要感受。
陆羽生在一个酒气冲天的唐代,他的同道并不多。与他唱和最多的皎然,是个和尚。和尚爱茶,最根本的动因是寺院禁酒,茶这种比中药药饮更有瘾头及品饮价值的植物才被空前放大,喝茶可以使人坐禅的时候不打瞌睡。
皎然宣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俗人饮酒,雅士喝茶,这是新名士论。郑板桥有一副对联说:“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这都是对陆羽茶道艺术的有力回应。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说,士大夫阶层饮茶之风,始于陆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陆羽之后的“茶”,确实变成了一门艺术,成为与“琴棋书画”相匹配的雅文化。扬之水在《“琴棋书画”图演变小史》里说,“琴棋书画”四事合成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风气肇始于宋代宫廷。王明清在《挥尘录》中提到,皇宫会宁殿有八阁东西对列,每阁各具名称,分别是琴、棋、书、画、茶、丹、经、香,宋高宗以雅文化怡情养性,并在宫廷教授相关技术,宫女的基本修养全在“八术”,正所谓“伊朱弦之雅器,含太古之遗美”。
“喝茶便雅”是宋人常见的观点,宋徽宗号召有钱人多喝点茶,脱脱俗气,“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喝茶指南《大观茶论》。
明皇子朱权,为了喝茶,专门发明了煮茶灶台,同样写了一本茶书,在南昌大兴茶道。明代江南的士大夫,则在美轮美奂的私家园林里,专门修建了精舍品茶。如今去逛苏州园林,昔年泡茶的场景犹在。清代的茶馆发展成遛鸟看戏的游乐场,曹雪芹不得不安排妙玉现身,教一教贾宝玉这样的世家公子,怎么喝才不糟蹋茶。但品味又怎么能短时间内培养得起来?
晚清时候,“打茶围”已经成为找妓女的代名词,民国年间胡适不得不在“打茶围”后,做出特别解释。去茶室喝茶不再是雅事,周作人只好把自己喝苦茶的家命名为“苦雨庵”。流浪在湖南的闻一多,写信抱怨说连日都在喝白开水,没有茶的日子难熬。到了台北的梁实秋,再也喝不到自己心爱的龙井茶,他摇头离开茶店。在北京的时候,梁实秋与闻一多到冰心家做客,发现连茶烟都没有,于是出门买。梁实秋意味深长地告诉冰心,一个读书人的家里,不能没有烟酒茶。这听起来,有点陶渊明在家置琴的意思。
在唐代,陆羽的茶艺还是前卫艺术,但在现在,品茶艺术已经深入人心,重提陆羽,是重拾断了很久的茶雅传统。因为,眼下的茶室几乎都变成了麻将馆的代名词。数年前,父母听说我开了茶室后,居然一夜都没有睡好,非得来昆明亲眼看到没有麻将桌才安心。
日本美学大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1906)里批评说,近代中国茶不过是一个很美味的饮品而已,与人生理念毫无关系。中国人长久以来苦难深重,已经被剥夺了对生命探寻的意义,他们变得暮气沉沉,注重实际,不再拥有崇高的境界,失去青春与活力的想象,失去了唐代的浪漫色彩,宋代的礼仪也没有了,庸俗不堪。
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遭遇的质疑,与一千年前张彦远遇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喝茶不过是小事一桩,与灵性境界有什么关系?”
“喝茶与令人讨厌的玄学思辨有何联系?”
“茶就是茶,还能是什么?”
“把茶变成某种奇怪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禅与日本文化》)
铃木大拙反问说,我们都知道有生必有死,那么何必那么隆重地搞葬礼、搞婚庆?
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我们视为庄重之事,为之举行隆重仪式,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那一个个场景,有些让人激动,有些让人沮丧。
“当我坐在茶室喝茶的时候,我是把整个宇宙喝到肚子里,我举起杯子之刻即是超越时空的永恒。谁说不是呢?茶道所要告诉我们的,远比保持万物的平衡,使它们远离污染,或者单纯地陷入宁静深思的状态要多得多。”
然而,从生命内在意义来说,一秒钟和一千年都一样重要。
陆羽说,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能做的,非常少。到了他那个时代,已经有人盖了最好的房子,缝了最好的衣服,酿了最好的酒。他还能做什么呢?
茶是上天留给陆羽的,他自然就要做到最好。
他一口气说了九个“非”,茶有九难,茶不在这一边,在另一边。
另一边就是工夫,就是修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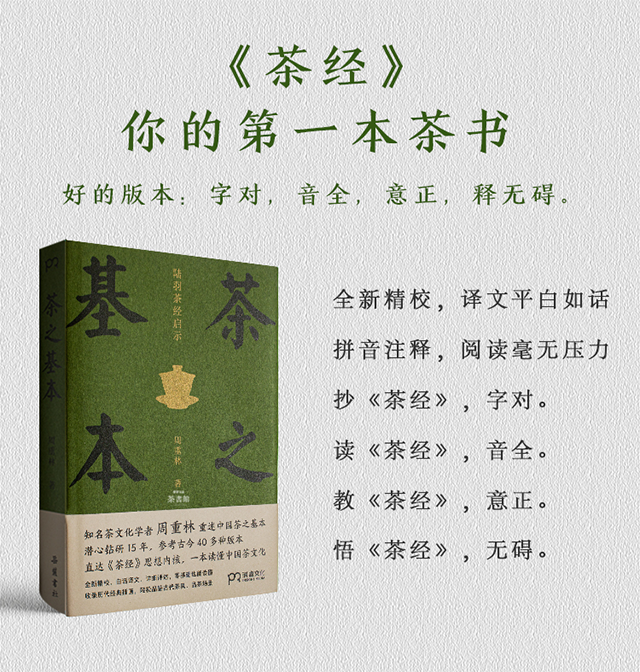
作者:周重林,图文来源:茶业复兴,经授权爱普茶网发布,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